每年超过三千部电影在全球各大影展中亮相,最终进入公众视野的往往不足百分之五。评审团的口味、发行商的判断、媒体的聚焦点,共同构成了一道隐形的筛选机制。那些在红毯之外、在颁奖礼后台、在展映单元末尾场次放映的作品,未必缺少艺术价值,它们只是在某个时刻与主流叙事擦肩而过。本文将目光投向2019年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一个以发掘新锐导演和实验美学著称的展映空间,在这里,有一批值得被重新打开的作品。
鹿特丹的另类逻辑
鹿特丹国际电影节从不以星光璀璨为目标,它的选片标准建立在”形式革新”与”边缘视角”之上。评审团更倾向于那些挑战常规叙事的作品,无论是非线性结构、反戏剧性处理,还是对影像本体的实验探索。这种偏好使得许多在商业层面难以被归类的电影得以在此呈现,但也导致它们在后续的传播中遭遇困境——艺术院线需要可辨识的标签,流媒体平台需要可预测的受众数据,而这些电影恰恰拒绝被简化定义。
2019年的鹿特丹影展恰逢全球独立电影融资困境加剧的时期,许多导演的第二部或第三部作品因缺乏资本支持而显得粗粝,却也因此保留了某种未经打磨的真实质感。影展期间,主竞赛单元”老虎奖”之外的”光明未来”单元和”大荧幕竞赛”单元,聚集了大量来自东南亚、东欧和拉美的创作者,他们的作品往往承载着复杂的地缘政治隐喻,却因语言和文化距离,在西方主流影评体系中失语。
被遮蔽的影像世界
《等待火车》(Aden · 2019)由苏丹裔荷兰导演Suzannah Mirghani执导,讲述一位流亡欧洲的非洲女性在陌生城市中寻找身份认同的故事。影片采用大量固定长镜头,将主角置于空旷的火车站、无人的广场和深夜的便利店中,环境音的设计几乎消解了对白的必要性。这种极简主义美学在鹿特丹获得了”光明未来”单元特别提及,但在后续发行中遭遇困境——它既不符合难民题材的煽情预期,也无法满足艺术片观众对视觉奇观的想象。导演拒绝将流亡经验简化为苦难叙事,反而通过影像的克制传达出一种悬置状态,这种暧昧性恰恰是其被低估的原因。
《盲琴师》(Hürkuş: Göklerdeki Kahraman · 2019)并非传统传记片,土耳其导演Kudret Sabancı将一位失明民间音乐家的人生重构为寓言式文本。影片以黑白摄影为主,偶尔插入彩色片段标记记忆与现实的界限。琴师演奏的安纳托利亚传统乐器萨兹,其音色贯穿全片,成为叙事的隐形线索。这部作品在鹿特丹”大荧幕竞赛”单元放映时,因其对声音设计的极致追求引发讨论,但最终未能进入主要奖项视野。评审团更青睐视觉冲击力强的作品,而《盲琴师》选择将听觉置于首位,这种反常规的感官分配使其成为影展中的异类。
《无名之地》(Nömadak TX · 2019)是哈萨克斯坦导演Adilkhan Yerzhanov的第七部长片,故事发生在苏联解体后的中亚荒原,一群失去土地的牧民在废弃工业区建立临时聚居地。导演以近乎纪录片的手法捕捉日常劳作的细节,却在关键段落插入超现实元素——沙尘暴中出现的巨型机械残骸,夜间篝火旁的集体幻觉。这种魔幻现实主义处理方式源自中亚口述传统,但在西方观众的观影经验中缺乏对应参照系。影片未能获得老虎奖提名,部分原因在于其文化编码过于密集,需要观众具备对后苏联时期中亚社会转型的基础认知。
《沉默的游行》(Sheer Qorma · 2019)由印度裔导演Faraz Arif Ansari执导,聚焦南亚穆斯林社群中的酷儿身份议题。影片采用章节式结构,每个段落以一道传统甜点命名,食物的制作过程与人物关系的演进形成隐喻对照。导演刻意避开了冲突戏剧化的处理,转而以细腻的家庭场景展现代际之间的理解与拉扯。这种温和的叙事策略在鹿特丹赢得了业内人士的赞誉,却也使其在竞争激烈的选片市场中显得”不够锋利”。发行商担心影片缺乏爆点,难以在社交媒体时代制造话题,最终仅在小范围艺术院线短暂放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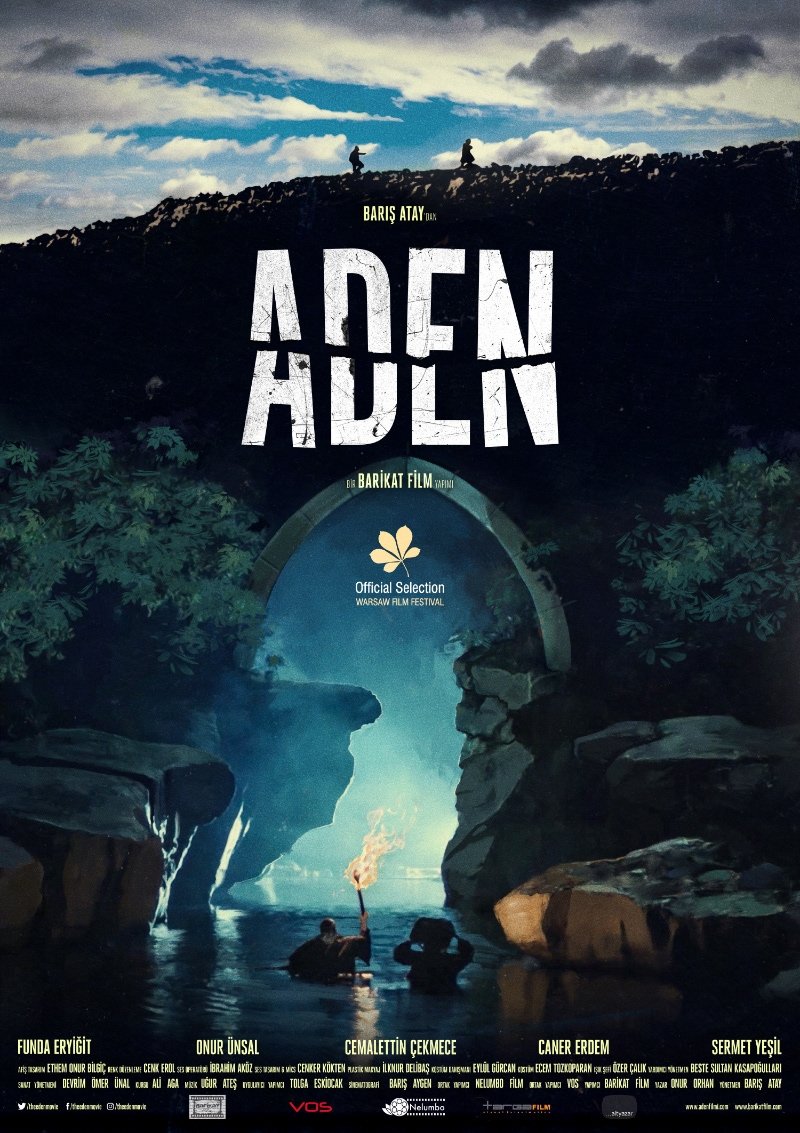
《边境回声》(Топот · 2019)来自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年轻导演Ksenia Elyan,影片以一位在矿区工作的女性地质学家为主角,她在勘探过程中发现了苏联时期的秘密档案。导演将这一发现作为引子,逐步揭开家族史与国家暴力记忆的交织。全片大量使用手持摄影,粗糙的画质与主角在荒野中的跋涉形成视觉同构。这部作品在鹿特丹的放映场次被安排在非黄金时段,观众席不足半满,但在场的影评人普遍认为这是当年被严重低估的作品之一。其未能获奖的原因,或许与评审团对后苏联题材的审美疲劳有关,也与影片拒绝提供简单道德判断的叙事立场相关。
《潮汐之间》(Entre la tarde y la noche · 2019)是墨西哥导演Oscar Ruiz Navia的第四部长片,故事围绕太平洋沿岸一个渔村的日常生活展开。导演几乎放弃了传统剧情推进,转而以观察式的镜头记录劳作、等待、闲谈的片段。影片的时间感极度延展,一场修补渔网的戏可以持续十分钟,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成为唯一的背景音。这种对”无事发生”的执着在鹿特丹引发了两极化评价——支持者认为这是对资本主义时间观的抵抗,反对者则质疑其是否跨越了沉闷与深刻的界限。影片最终与所有奖项无缘,却在影展结束后被法国《电影手册》列为年度十佳。
《夜行者》(Oray · 2019)由土耳其德国合拍,导演Mehmet Akif Büyükatalay以柏林的土耳其移民社区为背景,讲述一对年轻夫妇因宗教观念差异而产生的情感裂痕。影片的构图大量借鉴伊斯兰建筑的几何美学,对称与重复的视觉设计强化了主角被信仰规训的处境。导演在访谈中表示,他试图避开西方媒体对穆斯林群体的刻板叙事,既不美化也不妖魔化,而是呈现内部的多元与矛盾。这种立场的复杂性使得影片在鹿特丹赢得了尊重,却也限制了其在更广泛市场的传播——它既无法被归入”社会问题片”,也不符合”身份政治电影”的预期模板。
《房间尽头》(Gul Makai · 2019)聚焦阿富汗女性教育议题,但导演Amjad Khan选择了一种反常规的切入方式——影片并非线性传记,而是将不同时空的女性经验剪辑并置,形成一种集体记忆的视觉档案。黑白影像与彩色片段交替出现,旁白采用多种波斯语方言,这种复调叙事在形式上极具野心,但也导致观众在观影过程中需要付出更多认知努力。鹿特丹评审团对此片的评价分歧明显,最终未能进入获奖名单,但其在影展目录中的专题评论文章篇幅超过多数入围影片,可见业内对其价值的认可。
延伸观影线索
对上述作品感兴趣的观众,或许可以进一步探索这些相近气质的影片:《大象席地而坐》(An Elephant Sitting Still · 2018)、《大西洋》(Atlantics · 2019)、《地久天长》(So Long, My Son · 2019)、《野梨树》(The Wild Pear Tree · 2018)、《过昭关》(Passing Through · 2018)、《幸福的拉扎罗》(Happy as Lazzaro · 2018)。它们同样在某个时刻与主流视野擦肩,却在影展体系的边缘位置持续发光。
这些电影不会在算法推荐中占据显眼位置,也不太可能成为社交媒体的热门话题。它们需要观众主动寻找、耐心等待、反复思考。但正是这种观影体验的稀缺性,构成了它们独特的价值——在速度与奇观主导的时代,它们提醒我们,电影仍可以是缓慢的、暧昧的、拒绝被快速消费的艺术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