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五月,当戛纳海滨升起金棕榈旗帜,全世界的镜头都聚焦在红毯与主竞赛单元。但在这座电影朝圣地的诸多平行单元中——一种关注、导演双周、影评人周——始终存在着一批与主竞赛擦肩而过的作品。它们或因地缘政治考量被调配至边缘单元,或因题材敏感度未能进入评审团视野,又或单纯是排期与策略的牺牲品。这些电影并非质量不足,恰恰相反,它们往往携带着更激进的美学实验、更尖锐的社会批判,以及不愿向市场妥协的创作姿态。
戛纳的选片机制与遗珠成因
戛纳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每年仅收录约二十部作品,这个数字背后是复杂的政治平衡术。选片委员会需要在艺术性、话题性、地域代表性之间寻找平衡点,同时考虑发行商的市场预期与媒体的传播效能。导演双周与一种关注单元虽然同样在戛纳体系内,却往往成为”风险过高”作品的收容所——那些形式过于先锋、叙事过于破碎、或政治立场过于明确的电影,会被有意识地分流至此。
更隐秘的筛选逻辑在于”首映权”的争夺。许多艺术电影在完成后会面临多个影展的邀约,而戛纳通常要求世界首映权作为入选条件。那些已在柏林或鹿特丹亮相的作品,即便质量上乘,也会因程序原因被排除在外。此外,法国电影在主竞赛中的配额保护、英语片的天然优势、以及对”明星导演”的偏好,都让真正的独立电影难以突围。
被低估的影展佳作
《阿涅斯论瓦尔达》(Varda par Agnès · 2019)由阿涅斯·瓦尔达执导,这部纪录片在导演去世前数月完成,却未能进入主竞赛。影片以瓦尔达本人的口述为线索,回溯其六十年创作生涯中的关键时刻——从《五至七时的克莱奥》的女性凝视,到《拾穗者》的社会关怀。瓦尔达用手持DV在海滩上画出电影银幕的形状,用这种自反性的影像语言完成最后的创作宣言。影片被安排在特别展映单元,或许是因为戛纳不愿让纪录片占据竞赛席位,但这种分类本身就是对类型等级制的再生产。
《野梨树》(Ahlat Ağacı · 2018)由努里·比格·锡兰执导,虽入围主竞赛却空手而归。这部长达三小时的作品聚焦土耳其乡村知识分子的精神困境,父子两代人在债务、信仰与写作之间的撕扯,被锡兰以近乎布列松式的克制镜头呈现。大量静态长镜头捕捉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光影变化,对话密度远超一般艺术电影。评审团最终将金棕榈颁给了是枝裕和的《小偷家族》,后者更符合”人道主义温情”的叙事传统,而锡兰的哲学化表达显然不够讨喜。
《灼热之夏》(Un été brûlant · 2011)由菲利普·加瑞尔执导,这位法国新浪潮余脉的导演始终在主流视野之外。影片以1968年五月风暴为背景,用黑白16毫米胶片拍摄一对革命情侣的分合。加瑞尔拒绝对历史事件进行宏大叙事,转而将镜头对准床单褶皱、香烟烟雾与身体轮廓,政治的失败被转译为私人情感的崩解。这种”去政治化”的处理方式在当年引发争议,影片仅在一种关注单元展映,未能获得更广泛的讨论空间。
《山河故人》(Mountains May Depart · 2015)由贾樟柯执导,虽入围主竞赛却未获奖项。影片以1999年、2014年、2025年三个时间切片,呈现中国社会结构的剧变如何撕裂个体命运。贾樟柯在时间跨度中嵌入了语言的流失——第三段落中赵涛饰演的母亲与儿子已无法用共同语言交流,这种”失语”恰是全球化的精神症候。评审团或许认为其社会学意图过于明显,但正是这种”不够纯粹”的杂糅性,让影片具备了超越艺术电影圈层的传播潜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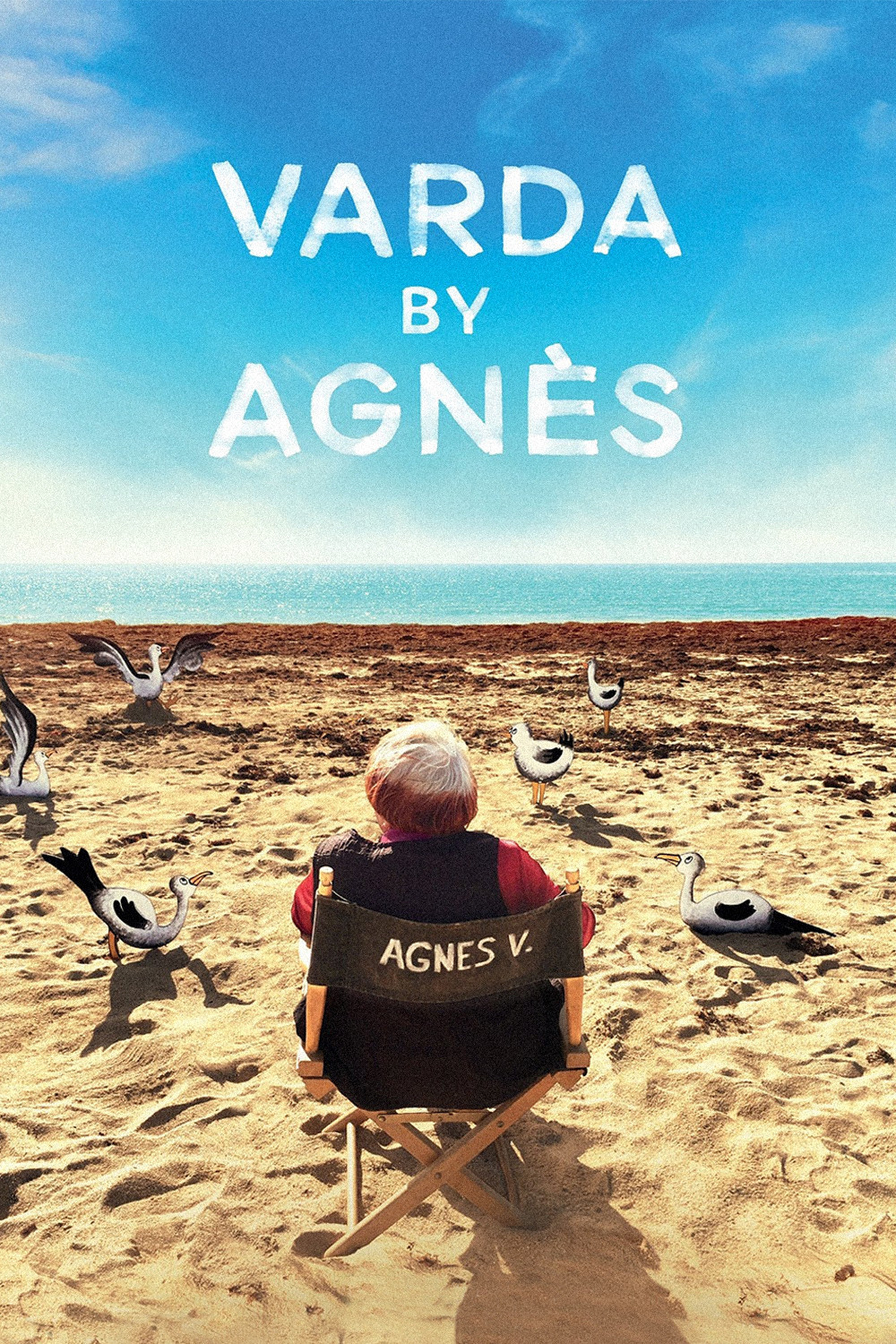
《阳光普照》(A Sun · 2019)由钟孟宏执导,这部台湾家庭犯罪片未能进入任何戛纳单元,却在金马奖横扫十一项大奖。影片以两个儿子——优等生与少年犯——的命运对照,撕开华人社会”望子成龙”文化的虚伪。钟孟宏用冷硬的警匪类型外壳包裹伦理困境,雨中追车戏的调度与情感爆发点的精准把控,展现出不输于韩国类型片的工业成熟度。戛纳或许认为其类型属性过强,但这恰恰是华语电影突破艺术片窠臼的有效路径。
《燃烧女子的肖像》(Portrait de la jeune fille en feu · 2019)由瑟琳·席安玛执导,虽入围主竞赛并获最佳编剧奖,但在金棕榈争夺中落败。影片讲述十八世纪布列塔尼海岸,女画家为贵族小姐绘制肖像期间的同性情感。席安玛用古典主义构图与自然光摄影,将女性凝视转化为一种对抗父权艺术史的方法论——画家与模特的关系不再是主客体二分,而是共谋式的互相创造。评审团主席亚历杭德罗·冈萨雷斯·伊纳里图或许更青睐男性导演的暴力美学,这部克制而炽烈的女性电影最终被《寄生虫》的类型完成度压制。
《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 · 2016)由玛伦·阿德执导,虽入围主竞赛却未能摘得桂冠。这部长达162分钟的德国喜剧以荒诞的父女关系为核心,父亲假扮成名叫托尼的”生活教练”介入女儿在罗马尼亚的跨国公司工作。阿德用长镜头捕捉尴尬时刻的延宕,将欧洲资本主义的精神空洞与家庭情感的断裂并置。金棕榈最终颁给了肯·洛奇的《我是布莱克》,后者更符合戛纳对社会批判的传统想象,而阿德的”不严肃”处理方式显然超出了评审团的舒适区。
《亚特兰蒂斯》(Atlantis · 2019)由瓦伦丁·瓦夏诺维奇执导,这部乌克兰科幻片在威尼斯地平线单元获奖,却未能进入戛纳视野。影片设定在2025年的顿巴斯战后地带,退伍军人在废墟中搜寻战争遗骸。瓦夏诺维奇用固定长镜头拍摄工业废土景观,每个镜头如同静帧摄影,演员在画面中缓慢移动如同雕塑。这种极端形式主义的处理让叙事几乎消失,战争创伤被转化为纯粹的视觉时间体验。戛纳选片人或许认为其过于晦涩,但正是这种”不可看性”构成了对战争表达的伦理姿态。
延伸观影线索
对这些影展遗珠感兴趣的观众,可以继续追踪以下作品:《盛夏》(Midsommar · 2019)、《隐秘的生活》(A Hidden Life · 2019)、《南方车站的聚会》(The Wild Goose Lake · 2019)、《痛苦与荣耀》(Dolor y gloria · 2019)、《小小乔》(Little Joe · 2019)。它们或在戛纳其他单元展映,或在同年其他影展获得认可,共同构成了一个被主流叙事遮蔽的平行电影宇宙。
这些电影的价值不在于填补某种缺憾,而在于提示我们:影展的筛选机制本身就是权力运作的场域。当我们将目光投向金棕榈之外,会发现更丰富的美学可能与更激进的思想实验。它们更适合那些愿意放弃观影舒适感、拒绝被动接受的观众——那些相信电影不仅是娱乐,更是认知世界的方法论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