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的评分系统从不完美。当一部作品在大众审美的坐标系里找不到准确位置时,它往往会被贴上”失败”的标签。这些被低估的冷门电影可能太过晦涩,可能太过冒险,也可能只是生不逢时。但在喧嚣的评分争议背后,它们常常携带着被忽视的诚意、未被看见的美学尝试,以及不肯妥协的创作姿态。
为何被误读
某些电影天生不讨好观众。它们拒绝提供清晰的情绪出口,不愿意用起承转合的叙事结构安抚期待,甚至故意在类型边界上制造模糊地带。这种创作策略在商业市场里几乎等同于自杀——观众走进影院期待一场惊悚片,却发现导演更关心人物内心的荒芜;打开一部科幻片,结果陷入哲学辩论的迷宫。
审美差异也会放大误解。某些影像语言需要特定的文化背景才能被准确接收,一旦脱离原生语境,它们的表达就会失焦。那些植根于冷门文化传统或边缘地域经验的小众独立电影推荐,在全球化的评分体系里常常遭遇冷遇。更不用说那些制作粗糙但想法惊人的艺术实验电影,它们用有限的资源完成了野心勃勃的尝试,却因为技术层面的不足被一票否决。
营销的缺位同样致命。当一部影片没有足够的宣发预算,它就很难找到真正的目标观众。错误的档期、模糊的类型定位、缺乏话题度的主创团队,这些因素让许多作品在上映之初就陷入被动。评分的形成往往发生在最初几周,一旦口碑崩盘,后续的挽救几乎不可能。
六部被忽视的作品
《海边的曼彻斯特》之后:《你能原谅我吗?》(Can You Ever Forgive Me? · 2018)
导演:玛丽埃尔·海勒
这部争议类型片佳作讲述一位落魄作家伪造名人信件的故事。梅丽莎·麦卡西的表演克制到近乎冷漠,她饰演的李·伊斯雷尔并非悲情主角,而是一个刻薄、自负、拒绝改变的中年失败者。影片没有给她安排救赎弧光,也不试图让观众同情她的犯罪行为。这种反类型的处理方式让许多观众感到不适——他们习惯在传记片里看到人性的温暖,而不是这种干燥的、几乎纪录片式的凝视。摄影机始终保持距离,连配乐都吝啬到几近于无。但正是这种克制,让影片成为关于创作者困境最诚实的注解之一。
《寂静的孩子》(The Silent Child · 2017)
导演:克里斯·奥佛顿
这部短片只有二十分钟,却在主流观众那里遭遇了冷遇。它讲述一个失聪女孩学习手语的过程,全片几乎没有对白,依赖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推进叙事。许多观众抱怨”看不懂””太闷”,评分系统里充满了三星以下的差评。但影片的价值恰恰在于它拒绝用煽情消费残障议题,而是用极简的影像语言展现沟通的本质。女孩学会第一个手语单词时的眼神变化,比任何台词都更有力量。这部豆瓣低分宝藏片后来拿下了奥斯卡最佳真人短片,证明评分系统的局限。
《安妮特》(Annette · 2021)
导演:莱奥·卡拉克斯
一部彻底的音乐剧电影,从第一秒到最后一秒都在唱。亚当·德赖弗和玛丽昂·歌迪亚用唱腔完成所有对话,甚至包括最日常的琐碎交流。这种形式上的极端主义吓退了大量观众,IMDb评分长期徘徊在及格线边缘。但卡拉克斯从未打算妥协:他用这种疯狂的形式解构了好莱坞童话、名人文化和父权暴力。影片后半段出现的木偶婴儿更是将超现实推向极致,观众要么接受这套逻辑,要么彻底放弃。摄影师用大量红色和绿色的高饱和度画面制造视觉侵略性,配合Sparks乐队诡异的旋律,整部电影像一场持续两个小时的感官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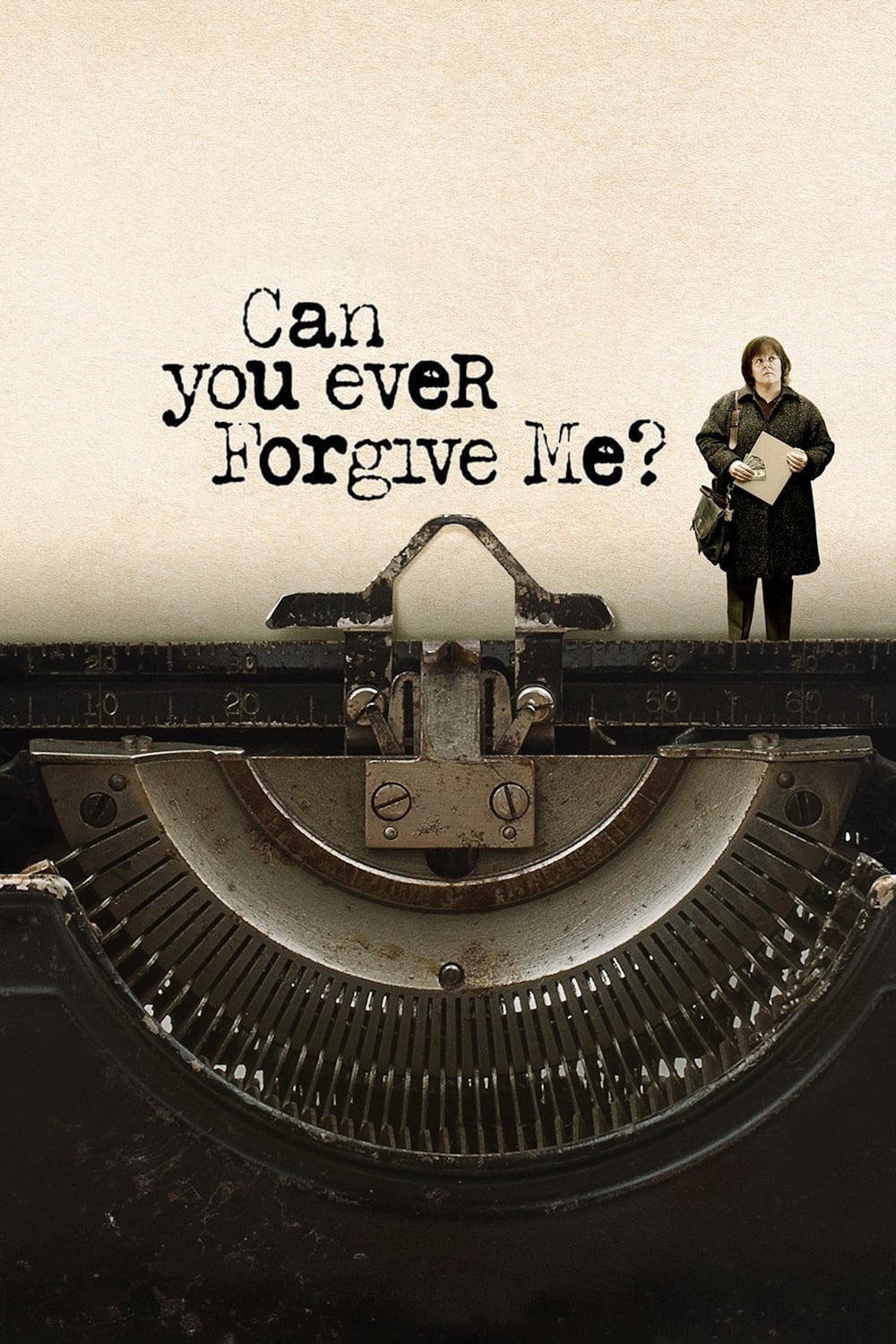
《黑煤,薄冰》之前:《白日焰火》(Black Coal, Thin Ice · 2014)
导演:刁亦男
虽然这部片拿了柏林金熊,但在豆瓣的评分一度跌至7.5分以下,大量观众抱怨”看不懂””节奏拖沓”。刁亦男把类型片的外壳拆解重组,将犯罪、爱情和存在主义困境糅合在东北工业区的寒冷背景里。他不在乎推理的严密性,更关心人物在暴力事件之后如何继续活着。廖凡饰演的警察像游魂一样在城市边缘游荡,他与桂纶镁之间的关系暧昧而危险,两人的每次对话都充满试探和躲闪。影片的影像风格极度风格化:蓝色调的夜景、工业废墟里的追逐、冰面上的尸体,这些画面构成了一种冷酷的诗意。但这种诗意需要观众主动进入,而不是被动接收。
《托尼·厄德曼》(Toni Erdmann · 2016)
导演:玛伦·阿德
一部长达162分钟的德语喜剧片,讲父女关系。许多观众在前半小时就放弃了——影片的节奏慢得不可思议,笑点藏在大量静默的长镜头里,父亲的恶作剧在某些人看来只是尴尬而非幽默。但阿德的野心在于用极端的篇幅展现情感的微妙变化。女儿在职场上的冷漠、父亲用荒诞方式的介入、两人之间逐渐建立的理解,这些都需要时间慢慢发酵。影片最著名的生日派对段落将尴尬推向极致,所有宾客脱光衣服却装作一切正常,这种超现实的处理既是喜剧也是对现代社会虚伪的控诉。
《鸟人》之后:《母亲!》(Mother! · 2017)
导演:达伦·阿伦诺夫斯基
可能是近年来评分最两极的电影之一。詹妮弗·劳伦斯饰演的女主人在自己家里遭遇越来越多不速之客,现实逐渐崩坏成噩梦。影片是一则关于创作、信仰和环境危机的寓言,但阿伦诺夫斯基用了最激进的方式呈现:手持摄影机几乎全程跟拍女主,制造令人窒息的压迫感;后半段的混乱场面像启示录般疯狂,暴力、宗教意象和超现实元素疯狂涌入。大量观众给出最低分,认为影片自大、晦涩、令人不适。但这种不适恰恰是导演的目的——他要让观众体验被侵占、被剥削的愤怒,而不是坐在安全距离外观看一个故事。
延伸观影
– 《海边的曼彻斯特》(Manchester by the Sea · 2016)
– 《皮囊之下》(Under the Skin · 2013)
– 《亚利桑那梦游》(Arizona Dream · 1993)
– 《圣鹿之死》(The Killing of a Sacred Deer · 2017)
– 《大象》(Elephant · 2003)
写在最后
这些电影的价值不在于它们完美,而在于它们拒绝安全。它们不迎合主流审美,不提供简单的情绪慰藉,也不在乎评分系统的奖惩。对于愿意冒险的观众来说,这些作品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在混乱的叙事里发现秩序,在晦涩的影像里感受诚意,在低分的标签下找到被忽视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