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时代都有不能被看见的影像。它们因触碰权力结构、撕开宗教面纱或呈现肉身真相而被驱逐出主流视野,在地下流通或永久封存。这些电影并非单纯的禁忌猎奇,而是以影像为刀,剖开社会溃疡,让沉默者发声。当审查制度试图抹除某种表达时,恰恰证明了这种表达的力量——它击中了某个不可言说的痛点,让既有秩序感到威胁。
压抑的机制:为何这些影像不被允许
政治隐喻的刺痛
极权体制最惧怕的从来不是直白的控诉,而是那些以寓言包裹的利刃。当影像用动物、神话或架空时空来映射现实权力运作时,审查者往往陷入两难:承认隐喻等于承认对号入座,不承认又无法阻止观众的自由解读。这类电影的危险在于,它们为观众提供了一套解码系统,让人学会透过表象看见本质。
历史创伤的再现
某些历史时刻被官方叙事有意简化或美化,任何试图还原复杂性的影像都会被视为”扭曲历史”。这类禁片往往不是捏造事实,而是呈现了被删除的记忆碎片——那些不符合宏大叙事的个体经验、被牺牲者的面孔、施暴机制的细节。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单一历史版本的挑战,提醒观众:真相从来不是铁板一块。
宗教权威的僭越
当镜头转向神职人员的欲望、教义的矛盾或信仰体系的暴力性时,宗教团体的反应往往比政权更激烈。这不仅因为宗教自视为道德守护者,更因为质疑信仰根基会动摇整个权力来源。这些影片的致命之处在于,它们用人性的复杂性消解了神圣的绝对性,让观众看见教义之下那些被压抑的肉身与欲望。
不可见的影像
《索多玛120天》(Salò, or the 120 Days of Sodom · 1975)
导演: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
帕索里尼将萨德笔下的极端施虐场景移植到墨索里尼政权末期的意大利,用排泄物、性暴力和仪式化酷刑构建了一个权力运作的寓言剧场。影片最令人不安的不是画面本身,而是施暴者的优雅从容——他们在古典音乐中朗读诗歌,在性侵害后讨论美学。这种文明外衣下的兽性恰恰是法西斯主义的真实面目。帕索里尼在影片完成后不久被谋杀,这部作品成为他对权力的最后控诉。
全球范围内曾遭禁映或删减,至今仍是许多国家的敏感之作
《悲情城市》(A City of Sadness · 1989)
导演:侯孝贤
侯孝贤用冷静的长镜头凝视1945至1949年的台湾,将官方不愿触碰的”二二八事件”编织进家族史。影片的政治性不在于控诉,而在于呈现——那些消失的知识分子、突然空掉的座位、再也无法归来的亲人。聋哑摄影师的设定极具隐喻:他无法言说,只能以影像记录,正如那个时代所有被噤声的人。侯孝贤拒绝煽情,让历史创伤以日常生活的断裂形式显现。
首部正面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华语电影,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感官世界》(In the Realm of the Senses · 1976)
导演:大岛渚
大岛渚以真实案件为蓝本,讲述艺伎阿部定与情人走向性爱自毁的过程。影片的争议不仅在于未经遮挡的性器官特写,更在于它将肉欲推向极致后揭示的虚无:当两个人试图通过占有对方身体来抵抗外部世界时,唯一的终点只能是死亡。大岛渚用这个故事刺穿日本社会对性的集体压抑,同时质疑爱情神话——所谓的至死不渝,可能只是另一种暴力。
因真实性爱场面在多国遭禁,底片需偷运出境完成后期制作
《我不在那儿》(I’m Not There · 2007)
导演:托德·海恩斯
这部关于鲍勃·迪伦的”非传记片”用六个不同性别、种族、年龄的演员扮演主角,拆解了传记片的权威性。影片真正的禁忌不在题材,而在形式:它拒绝提供一个稳定的主体,让观众无法将”迪伦”固定为某种符号。在传记片被用作造神工具的时代,这种解构姿态本身就是反叛。海恩斯借此追问:当我们讲述一个人的生命时,是在还原真相,还是在制造新的神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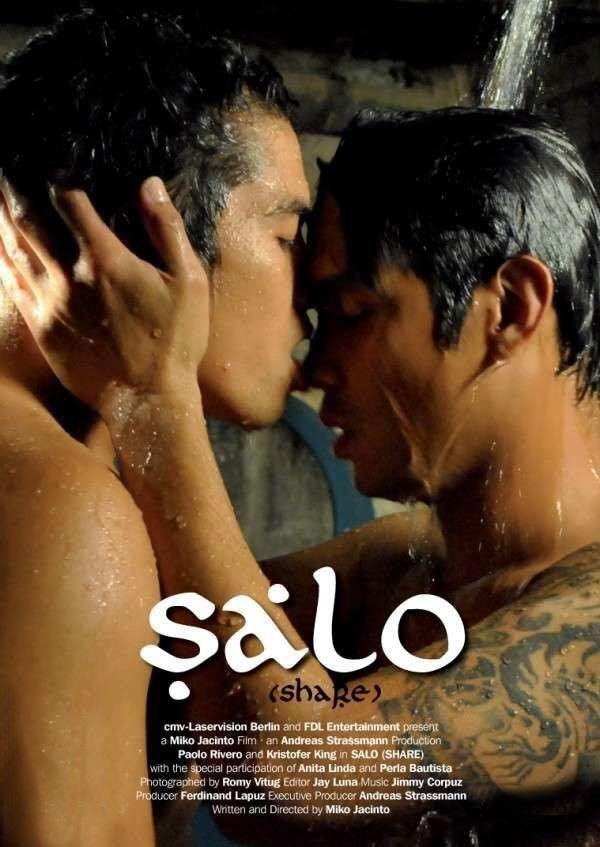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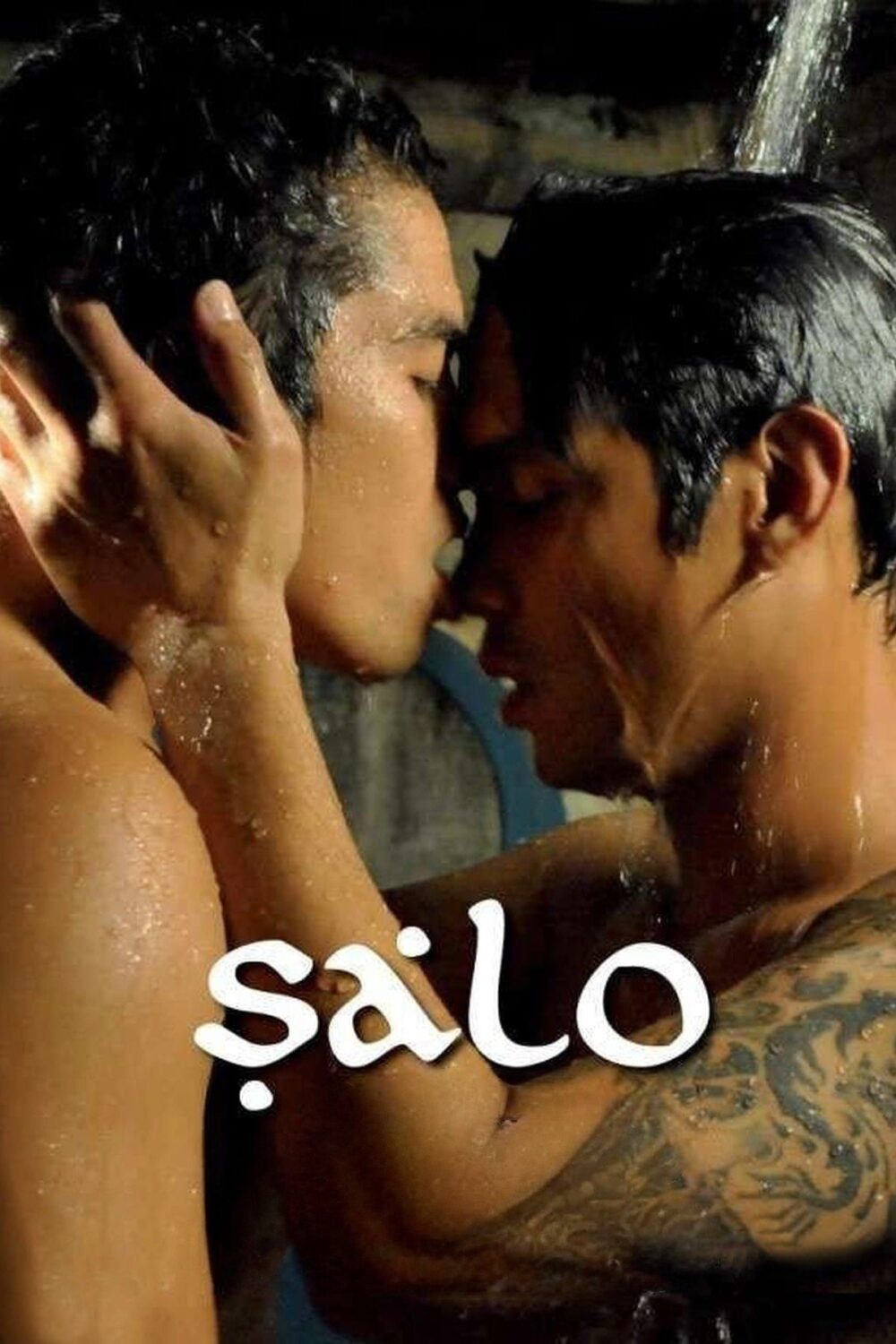
凯特·布兰切特凭男性角色获威尼斯最佳女演员奖
《教宗的承继》(The Two Popes · 2019)
导演:费尔南多·梅里尔斯
表面是两位教宗的对话录,实则是对天主教会权力更迭与教义危机的深度剖析。梅里尔斯让本笃十六世与方济各在虚构的密室对话中,讨论教会性侵丑闻、信仰与政治、传统与革新。影片的大胆之处在于将神职人员去魅,让他们以普通老人的身份坦露疑虑与软弱。这种人性化处理触怒了保守派,却也让观众看见宗教权威之下那些被掩盖的裂隙。
多个天主教国家曾抵制放映,认为影片亵渎教宗形象
《我杀了我妈妈》(J’ai tué ma mère · 2009)
导演:格扎维埃·多兰
多兰19岁时自编自导自演的处女作,以极端主观的视角呈现青春期儿子对母亲的爱恨交织。影片的冒犯性在于它毫不避讳地展现子女对父母的厌恶——那些被家庭伦理压抑的真实情感。多兰用分屏、慢镜、强烈色彩构建了一个情绪化的影像空间,让观众与主角一同经历那种想要逃离又无法割舍的撕裂。这种对家庭关系的祛魅在部分保守社区引发争议。
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三项大奖
《惊惧》(Angst · 1983)
导演:杰拉德·卡格尔
奥地利导演卡格尔用手持摄影跟随一个刚出狱的精神病患者,记录他入侵民宅、杀害三人的全过程。影片的极端性不在于暴力本身,而在于导演对施暴者主观视角的完全认同——摄影机成为凶手的眼睛,观众被迫与杀人者共享感知。卡格尔拒绝提供道德评判或心理分析,只是冷酷地呈现暴力的机械性。这种去情感化的残酷在德国等国家引发禁映。
基于真实案例改编,在多国因过度暴力遭禁
《烈日灼人》(Burnt by the Sun · 1994)
导演:尼基塔·米哈尔科夫
米哈尔科夫将斯大林大清洗时期浓缩进一个夏日午后,让革命英雄科托夫在家人团聚的田园牧歌中被秘密警察带走。影片的残忍在于对比:孩子们的笑声与卡车驶来的轰鸣交织,阳光下的拥抱成为永别前的最后温存。导演不渲染暴力场面,却让观众在日常生活的突然断裂中感受历史创伤。这种对苏联历史的重新审视在俄罗斯国内引发激烈争论。
获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在部分前苏联国家遭抵制
延伸观影
– 《坏教育》(La mala educación · 2004)
– 《粉红色火烈鸟》(Pink Flamingos · 1972)
– 《撒旦探戈》(Sátántangó · 1994)
– 《浪潮》(Die Welle · 2008)
– 《杀人回忆录》(Memoir of a Murderer · 2017)
影像的韧性
这些被压抑的影像最终告诉我们:审查制度可以阻止电影公映,却无法抹除它们提出的问题。当权力试图定义什么可以被看见时,那些不可见之物反而获得了更强的生命力。它们适合那些愿意直面不适、拒绝被投喂答案的观众——不是为了猎奇,而是为了理解世界的复杂性,理解人性在极端处境下的扭曲与坚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