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多以战争、屠杀为题材的纪录影片中,很少有作品像《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这样令观众极度不适,却又无法移开目光。这部由约书亚·奥本海默执导的印尼屠杀纪录片,放弃了传统的“证言+资料画面”结构,反而邀请当年的杀人者自己来“重演”他们的罪行。这样近乎荒谬的设定,让人一度怀疑纪录片是否有权利、甚至有必要“表演”真实的历史恶行。但正是这种极端的重现,让《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成为一部被主流视野长期忽视,却难以替代的影像实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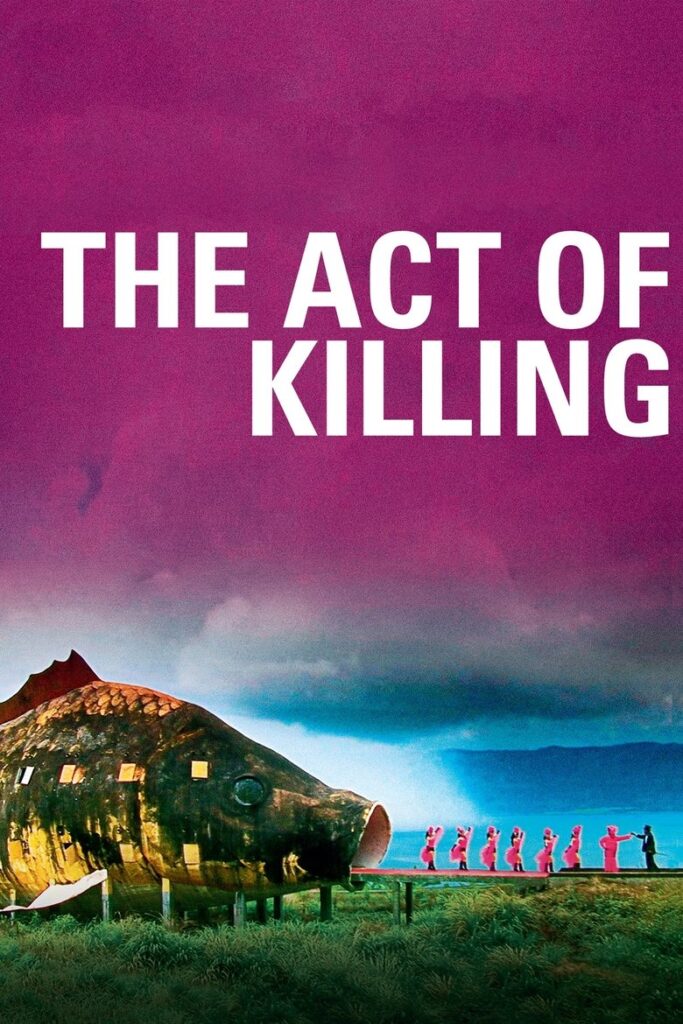
这部电影真正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彻底打破了观众对“反思历史”的惯性期待。导演没有选择幸存者的泪水与控诉,而是给了加害者一把摄像机与舞台,让他们用自恋、荒唐甚至滑稽的方式,去重构自己的残暴往事。这种“表演”并非轻浮或者戏谑,相反,它让人看到权力如何腐蚀记忆,如何让自以为英雄的凶手在镜头前毫无愧色地展示杀戮。影片中,暴力的记忆并不只是被回忆出来,而是以一种扭曲的娱乐、表演和自我神化的方式被重新制造出来。
许多观众第一次看到这样的纪录片时,会觉得愤怒甚至反感:纪录片不是应该尊重事实吗?导演为什么要让恶人如此肆意表演?这正是《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的悖论性美学——它拒绝道德说教,却让邪恶的本质在光天化日下赤裸裸地展现。导演的镜头既没有谴责,也没有宽恕,而是冷静地记录下加害者的荒谬自述,让历史的真相在镜头与表演的夹缝中自行显现。
在艺术片和纪录片的交界上,这种做法极具争议。很多主流影评认为它“过于猎奇”,甚至“丧失了对受害者的同理心”。但如果我们放下传统的道德审判,会发现导演其实在用一种极其残酷的方式追问:如果罪恶可以被娱乐化、被自我神化,那历史的真实还剩下什么?这种不适感,正是电影的最大价值。它不再是简单地“还原真相”,而是直面人性在极端情境下的变形。
《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的视觉风格极为夸张,充满了戏剧化的色彩与布景,甚至让人联想到现实与幻觉的边界。例如杀人者穿上华丽服装,重演杀戮场景时,既像在扮演电影明星,也像在参与一场病态的狂欢。导演让观众体验到历史记忆如何被权力操控、被娱乐工业消费。这种影像风格,极大地拓展了纪录片的可能性,也让人想起“《楚门的世界》之前:主控社会为何成为电影母题”中对现实与虚构边界的讨论,只不过这里是以真实的死亡与罪行为代价。
这类影片之所以不被主流理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挑战了观众的道德舒适区。很多人更倾向于接受明确的善恶对立、受害者与加害者泾渭分明的叙事方式。而《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则让加害者成为“主角”,让他们自导自演自己的罪行。这种结构既不是受害者自述的“疗愈”,也不是加害者的“赎罪”,而是一种介于表演、反思与自恋之间的灰色地带。观众无法轻易获得情感上的释放,反而被迫不停追问:什么是历史的真相?什么是真正的悔悟?
与之呼应的另一部值得被重新发现的纪录片,是波兰导演帕维乌·洛兹马尔斯基的《影子之下 In the Shadow of the Sun (2015)》。这部作品同样不走寻常路,聚焦于东欧历史创伤,通过实验性影像与声画分离的手法,揭示了集体记忆如何被消解与重构。影片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者”,只有断裂的影像和重复的声音,让观众在迷失与不安中体会被历史侵蚀的无力感。它和《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一样,用极端的美学和结构逼迫观众思考:纪录片究竟能否“复原”那些已经被扭曲的历史?
在全球范围内,像这样的“被忽视”的纪录片,往往被主流市场边缘化。它们不提供安慰、不制造希望,反而把观众推向难以承受的历史现场。很多时候,这类作品甚至比最激烈的虚构片更加令人不安。正如有影评人谈论“《渺生一页》:女性欲望在影像中如何被重新书写”时提到的,真正的艺术片往往是对主流叙事的反叛。它们不讨好观众、不追求情感共鸣,只是固执地守护着对复杂现实的多维凝视。
最终,《杀戮演绎 The Act of Killing (2012)》之所以值得被重新发现,是因为它用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撕开了历史记忆的表层。导演没有把历史罪恶“复原”成可泣可叹的悲剧,而是让罪恶本身在“表演”与“观看”中变得无法逃避。它让我们意识到,纪录片不只是还原过去,更可以暴露人性中最深层的扭曲与盲点。对于那些渴望拓宽影像边界、愿意直面复杂现实的观众来说,这样的电影或许才是纪录片最需要被重新看见的存在。
